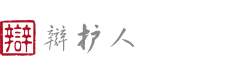3月19日,针对新媒体背景下“律师公开言论和案件信息使用”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执业纪律与执业调处委员会发布了的“第9号规范执业指引”。该指引填补了律师行业指导规范的一些空白,对于促进律师公开言论和案件信息使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维护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具有积极意义。
但也有个别条文值得商榷。例如,其中第八条规定:“在判决生效之前,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利用包括微博、博客在内的各种方式公开案卷材料、辩护词、代理词,或者向无关人员泄露办案信息。”该规定,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审判公开原则及司法公开的大趋势明显不符。
根据我国《宪法》第125条、《刑事诉讼法》第11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所谓“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主要是指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这些案件依法不公开审理,律师的保密义务持续到诉讼结束之后。除这些特殊情况外,对于公开审理的案件,律师的保密义务原则上至一审公开开庭时即告解除。
这是因为,所谓审判公开,不仅是指对当事人公开,还包括对社会公开,即允许一般社会公众旁听,允许记者等媒体人士到庭旁听和采访报道。因此,一旦进入公开开庭审理,案件信息即宣告公开,律师的保密义务随之解除。前述指引第八条把律师对案件信息的保密义务延伸到“判决生效前”,等于要求律师在公开开庭审理后仍要承担保密义务,这显然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审判公开原则有悖。
审判公开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法治原则,其意义在于保障审判的民主性、公正性,将审判纳入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防止司法腐败和专横,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增强司法的公信力。在此基础上,近年来,中国法院大力推进司法公开,不仅要求庭审公开、裁判文书上网公开,还强调立案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审务公开等,着力打造阳光司法。对一些典型案件,人民法院还通过网络或微博进行直播,收到良好效果。因此,不适当地限制律师发布案件信息,与司法公开的大趋势也相悖。
当然,即使在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后,对律师的庭外公开言论及对案件信息的发布,也并非没有限制。因为,律师仍负有谨慎司法评论的义务,不能“人身攻击”及“干扰和影响司法公正”;对当事人也负有忠实义务,非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公开其“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等。
另外,参照其他国家的律师行业规范,即使在公开开庭审理之前,律师也并非绝对不可以发布任何案件信息。例如美国,根据《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2004)》3.6条,“正在参与或者曾经参与某事务的调查或者诉讼的律师,如果知道或合理地应当知道其所作的程序外言论会被公共媒体传播,并对裁判程序有严重损害的可能,则不得发表这种程序外言论”,但3.6条(b)仍规定有多项例外,允许律师对一些事项发表评论。同时,3.6条(c)规定了所谓“回应权条款”,即“尽管存在(a)款的规定,如果一个普通律师会认为需要保护某委托人免遭最近非因该律师或者该律师的委托人对案情的宣传而带来的严重不当损害,则律师可以进行有关陈述。根据本款进行的陈述,应当限制在为减轻上述最近的不利宣传带来后果所必需的范围内。”根据“回应权条款”,针对他人(包括侦控机关)公开发表的不利于委托人的言论,律师有权发表针对性言论,包括公布必要的案件信息。
很明显,前述第9号规范执业指引第八条的限制性规定,是不适当地扩大了律师的保密义务,过度限制了律师的言论自由。而且,该规定使用有“各种方式”“无关人员”“办案信息”等不确定的概念,执行中难免尺度不一,且容易给个别地方司法机关对律师实施职业报复提供口实。一旦被恶意滥用,还会妨害到律师辩护权、代理权的合法行使,进而损害司法公正、法治尊严。
规范律师庭外言论,强调保密义务,有其必要,但不能无限扩大。律师同样是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行业规范对这种权利的限制,必须保持在合法、必要的限度内,并以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为根本宗旨。
(作者为北京学者)


| 上一篇: 非法证据排除“难”在哪儿 |
| 下一篇: 在死刑复核中坚守法治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