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86号]【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醉酒驾车连续冲撞致多人伤亡的如何定罪处罚?
韩维中 王飞 刑事审判参考 2015-0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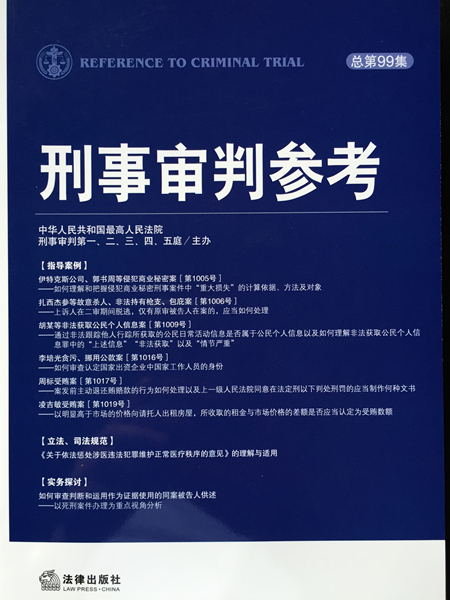
▍文 韩维中 王飞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71集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伟铭,男,1979年5月9日出生,成都奔腾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员工。因涉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2008年12月26日被逮捕。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8年5月,被告人孙伟铭购买一辆车牌号为“川A43K66”的别克轿车。之后,孙伟铭在未取得驾驶证的情况下长期驾驶该车,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同年12月14日中午,孙伟铭与其父母为亲属祝寿,大量饮酒。当日17时许,孙伟铭驾驶其别克轿车行至成都市成龙路“蓝谷地”路口时,从后面撞向与其同向行驶的一辆比亚迪轿车尾部。肇事后,孙伟铭继续驾车以超过限定的速度(60公里/小时)行驶。行至成龙路“卓锦城”路段时,越过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与对面车道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相撞,造成其中一辆长安奔奔轿车上的张景全、尹国辉夫妇和金亚民、张成秀夫妇死亡,代玉秀重伤,以及公私财产损失5万余元。经鉴定,孙伟铭驾驶的车辆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公里/小时;孙伟铭案发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135.8毫克/100毫升。案发后,孙伟铭的亲属代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1.4万元。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孙伟铭在未领取驾驶证的情况下,长期违法驾驶机动车辆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其醉酒后驾车行驶于车辆和人群密集之处,对公共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且在发生追尾事故后,置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继续驾车超速行驶,跨过道路上禁止超越的中心黄色双实线,与对方正常行驶的多辆车辆相撞,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及公私财产损失数万元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孙伟铭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孙伟铭以其主观上不具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一审判决定罪不准,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孙伟铭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孙伟铭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获得被害方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
二审期间,孙伟铭之父孙林表示愿意代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经法院主持调解,孙林代表孙伟铭与被害方达成民事赔偿协议,积极筹款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100万元(不含先前赔偿的11.4万元),取得被害方一定程度的谅解。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伟铭无视交通法规和公共安全,在未取得驾驶证的情况下,长期驾驶机动车辆,多次违反交通法规,且在醉酒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不计后果,继续驾车超限速行驶,冲撞多辆车辆,造成数人伤亡的严重后果,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孙伟铭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但鉴于孙伟铭是间接故意犯罪,与直接故意驾车撞击车辆、行人的犯罪相比,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其犯罪时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案发后真诚悔罪,并通过亲属积极筹款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可从轻处罚。原判认定的事实和定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维持一审判决对被告人孙伟铭的定罪部分;
2.撤销一审判决对被告人孙伟铭的量刑部分;
3.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主要问题
1.被告人孙伟铭醉酒驾车连续冲撞致多人伤亡,应如何定罪?
2.对被告人孙伟铭如何适用刑罚?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孙伟铭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本案发生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对被告人孙伟铭的行为如何定罪,在审理中争议较大:一种意见认为,孙伟铭醉酒驾车肇事,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伟铭醉酒驾车,连续冲撞多辆轿车,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正确区分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们认为,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应认定孙伟铭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要严格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来认定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的性质。醉酒驾车肇事客观上表现为醉酒驾车,造成他人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危害了公共交通安全,这同时符合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征,故从客观方面很难进行区分。对此类行为的准确定罪,更为重要的是分析行为人肇事时的主观心态。如果是故意,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如果是出于过失,则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实践中,醉酒驾车犯罪行为人往往不希望也不积极追求伤亡结果的发生,其罪过形式系放任的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较难把握。一般而言,应结合行为人是否具有驾驶能力、是否正常行驶、行驶速度快慢、所驾车辆的车况如何、路况和能见度如何、案发地点车辆及行人多少、肇事后的表现,以及行为人关于主观心态的供述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在不同的个案中,行为人对醉酒驾车造成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态不同,故不能认为醉酒驾车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一概是故意或过失,进而一律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交通肇事罪。
第二,要从立法目的角度正确理解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条文之间的关系。虽然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和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属于刑法第二章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但“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是对“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等行为的兜底,而不是对整个刑法第二章所有条款的兜底。故从立法目的看,不能得出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第一百一十五条完全适用于醉酒驾车犯罪行为的结论。司法实践中,不能将这两个条款无限制地扩大适用于所有醉酒驾车犯罪。从刑法规定看,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是指那些与“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具有同等严重破坏性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而不是泛指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一般情况下,醉酒驾车肇事和采用放火、决水、爆炸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危害公共安全性质上有差异,不能把醉酒驾车肇事简单地一律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醉酒驾车肇事行为在何种情况下与放火、决水、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在性质上相当,要在具体案件中根据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环境等情况来具体分析判断,不能单纯以危害后果来判断醉酒驾车肇事行为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要重视把握量刑平衡与准确定罪的关系。由于刑法没有将醉酒驾车行为本身规定为犯罪,对于醉酒驾车造成人员伤亡的犯罪,如果一律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则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醉酒驾车未肇事,或者虽然肇事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的,不能定罪;而醉酒驾车造成人员伤亡的,哪怕只是造成一人重伤,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至少都要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显然,对后一种情形的处罚明显过重,有违罪刑均衡原则。同时,行为人在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撞击车辆或行人,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明显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如果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理,一般情况下,最多只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处罚明显偏轻,不仅罪刑不相适应,而且也起不到有效的警示和预防作用,不足以遏制当前日趋严重的醉酒驾车犯罪现象。
本案中,被告人孙伟铭未经合格的机动车驾驶培训并取得驾驶证,且在长期驾驶中多次违反交通法规,说明其并不具备正常驾驶能力。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国家标准(GBl9522―2004)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100毫升的,属于醉酒驾车。孙伟铭案发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35.8毫克/100毫升,属于严重醉酒。孙伟铭在不具备正常驾驶能力和严重醉酒的状态下,驾车行驶于车辆密集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人都能够认识到其行为很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危害公共交通安全,孙伟铭作为心智健全的人,也能够认识到其行为的高度危险性。尤其是孙伟铭驾车与其他车辆发生追尾事故后,其完全能够认识到自己醉酒驾车极可能再次撞击其他车辆或行人,但孙伟铭不仅不及时停车,有效防止再次肇事,反而继续驾车以超过限速2倍以上的速度行驶,以致越过道路上禁止超越的黄色双实线,连续撞击对方车道上正常行驶的其他4辆轿车,造成数人伤亡的严重后果。综合孙伟铭的驾驶能力、行驶速度、行驶状况、肇事地点的车辆状况及其肇事后的表现等情况,足以认定孙伟铭对该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心态,故其主观上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需要指出的是,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中,行为人之所以自信,是因为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其自以为可以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合理依据,只是过高地估计了这些因素对于防止危害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而已,因而未能防止危害结果发生。但在本案中,孙伟铭既无合格的驾驶能力,也无丰富的驾驶经验,其在无驾驶能力的情况下,醉酒驾车高速行驶于车辆密集的城市道路上,危害结果的发生近乎必然,故客观上完全不存在使其自信可以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合理依据。其主观罪过形式不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对其行为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二)被告人孙伟铭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不应适用死刑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就醉酒驾车肇事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而言,在决定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特别是决定是否适用死刑时,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具体而言,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注意把握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一般情况下,醉酒驾车犯罪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犯罪。与以制造事端为目的而恶意驾车撞人并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直接故意犯罪相比,此类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因此,在决定刑罚时,不能将此类犯罪与直接故意犯罪完全等同。
第二,要注意把握行为人的实际辨认和控制能力。虽然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客观地看,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实际上都有所减弱。行为人犯罪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状况,足以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而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正是量刑的重要依据,因此,一般情况下,考虑到醉酒驾车犯罪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实际有所减弱,处理上要体现区别。
第三,注意把握民事赔偿与量刑的关系。刑法规定,犯罪分子应当赔偿由于其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故醉酒驾车行为人依法赔偿其犯罪行为给被害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其法定义务。行为人履行赔偿义务,并不影响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但是,行为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的,不仅反映出行为人认罪、悔罪的诚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这不是“花钱买刑”。所谓“花钱买刑”,是指犯罪分子利用钱财,通过不正当手段逃避刑事追究或获得从轻处罚。“花钱买刑”的犯罪分子并非真诚认罪、悔罪,与上述情况存在本质区别。故司法实践中,在对醉酒驾车犯罪行为人量刑时,既要考察其是否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了被害方的经济损失,又不能简单地把赔偿经济损失作为从轻处罚的理由。对于醉酒驾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分子,如果罪行极其严重的,即使其赔偿了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也不能从轻处罚。
第四,要严格执行死刑政策,慎重适用死刑。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是否属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从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认定,不能只看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行为人醉酒驾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虽然往往情节比较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但此类犯罪一般系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结果发生,与蓄意杀人和恶意驾车撞击车辆或行人的直接故意犯罪不同。相比之下,此类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因此,醉酒驾车犯罪行为人一般不属于刑法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因而不属于适用死刑的对象。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出发,一般不适用死刑。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犯罪行为均不适用死刑。对于醉酒驾车犯罪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的,如醉酒驾车肇事后,不顾拦阻,或抗拒检查、抓捕,或为逃避处罚,继续驾车撞击车辆、行人,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也有依法判处死刑的余地。
本案被告人孙伟铭醉酒驾车,连续冲撞多辆轿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及数万元的财产损失,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严惩,但鉴于其系问接故意犯罪,与直接故意犯罪相比,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系在严重醉酒状态下犯罪,驾驶车辆的控制能力实际有所减弱;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被害方的谅解。综合本案的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孙伟铭尚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因此,二审改判其无期徒刑是适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