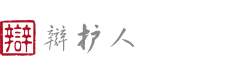▍作者 邓庆文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s
近日,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在何华芳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中,公然剥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庭审的权利,这一做法不仅突破了刑诉法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本保障,更暴露了司法实践中以"程序便利"之名行"程序暴力"之实的危险倾向。当法庭以"滥用诉讼地位"为由将被害人驱逐于司法程序之外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某个个案的程序失范,更是司法权力对程序正义底线的肆意践踏。
一、诉讼主体资格的司法僭越:当法庭成为程序审查者
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定位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赋予其参加庭审、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回避等十余项法定权利。苍南法院以"尚未开庭即否定被害地位"的逻辑,实质上是以司法裁判权提前完成了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判断。这种将程序参与权与实体主张捆绑审查的做法,无异于要求当事人在进入法庭前就自证主张绝对成立,彻底颠倒了"程序保障实体"的诉讼逻辑。
司法解释明文规定被害人陈述具有独立证据地位,但这绝不意味着法院可以将被害人降格为普通证人。证人作证义务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分属不同维度,法庭以"被害人应当承担控诉义务"为由排除其参与庭审,本质上是对刑诉法第191条被害人陈述权的曲解。当合议庭将被害人参与庭审的资格与其诉讼主张的合理性挂钩时,已然构成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司法审查,这种权力扩张已突破刑事诉讼法设定的程序框架。
二、司法权力的程序性越界:当程序工具主义吞噬法治根基
从诉讼架构观察,苍南法院的做法实质是混淆了程序规则与实体裁判的界限。刑诉法第110条规定的控告权是选择性权利而非强制性义务,司法解释第64条更未创设被害人必须积极控诉的法律责任。法庭将被害人未充分履行控诉职能作为剥夺其程序权利的依据,实属对法律条文的错位适用。这种以程序手段变相惩罚"不配合"当事人的做法,暴露了将司法程序异化为权力规训工具的深层危机。
比较同类案件处理可见,即便在被害人陈述与公诉主张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北京、上海等地法院仍严格保障其全程参与诉讼的权利。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明确:被害人对犯罪事实的认知差异不影响其程序主体资格。苍南法院创设的"被害人资格审查"标准,不仅缺乏法律依据,更与全国司法机关的普遍认知相悖,这种做法正侵蚀着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三、法治生态的修复路径:程序正义的回归之道
程序权利的保障不应受实体主张正确性的反向制约。被害人是否"滥用诉讼地位"的判断,必须经过完整庭审程序的检验,而非由法庭在程序启动阶段径行认定。当合议庭以"未达控诉标准"为由拒绝被害人参与庭审时,实际上是在用程序排除的方式替代实体审理,这种"未审先判"的逻辑彻底瓦解了对抗式诉讼的根基。
司法权威的塑造有赖于对程序正义的敬畏。法院在追求诉讼效率时,绝不能以牺牲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为代价。当前亟需检察机关依据刑诉法第209条,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及时纠偏。苍南法院的违法决定应当予以撤销,程序违法责任人员应当受到司法问责。唯有让违法者付出成本代价,才能重建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任基础。
当法庭的槌声不再为程序正义而鸣响,司法公正的大厦终将沦为权力的废墟。苍南法院的这场程序失范警示我们:任何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轻慢,都是对法治根基的动摇。期待浙江三级法院系统能以刮骨疗毒的勇气直面问题,用对程序正义的坚守重塑司法公信,莫让个案的程序溃堤演变为司法公信的全面决堤。


| 上一篇: 法官亲属辩护权受阻:司法随意化阴影下的法治之殇 |
| 下一篇: 警界精英陨落背后的程序正义之问 |